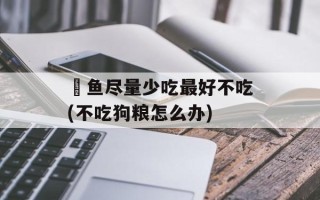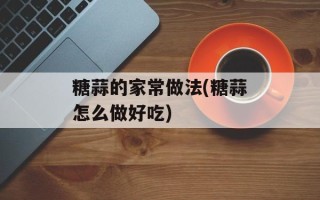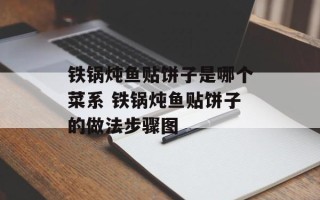今天给各位分享王越死亡时间的知识,其中也会对王越病逝了吗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
一、三国大时代4王越什么时候死
1、三国大时代4黑阎王死亡时间大概是一分钟。
2、加入汉朝,可在篷莱招复国武士,汉献帝在许昌皇宫。
3、加入董卓,可在朔方招羌弓骑兵,董卓在云中一个房里。
4、加入司马懿,可在云中招苍狼兵,司马懿在宛城一个房里。
5、加入张角,可招黄巾兵,在张掖。
6、加入马克斯,可招罗马兵,马克斯在陇西。
7、加入孟获,可招象骑兵,在兴古。
8、加入义军,可招武士,王越在建安。
9、加入黑旗军,可招黑旗兵,黑阎王在长白山。
二、王越传文言文
1.文言文阅读段匹磾,鲜卑人也,父务勿尘,谴军助于东海王越征讨有功
段匹磾,鲜卑人也,父务勿尘,谴军助东海王越征讨有功……
段匹磾,鲜卑人也,父务勿尘,谴军助东海王越征讨有功……
释义:段匹磾,鲜卑族人,父亲段务勿尘,派兵协助东海孝献王司马越征讨有功……
据《晋书·段匹磾传》记载:段匹磾,东部鲜卑人也。种类劲健,世为大人。父务勿尘,遣军助东海王越征讨有功,王浚表为亲晋王,封辽西公,嫁女与务勿尘,以结邻援。怀帝即位,以务勿尘为大单于,匹磾为左贤王,率众助国征讨,假抚军大将军。(释义:段匹磾,东部鲜卑人。祖上世代为鲜卑段部部落首领。父亲段务勿尘,由于派兵助东海王越征讨有功,晋朝将领王浚向中央建议,封务勿尘为辽西公,并将女儿嫁给务勿尘,以结援手。怀帝即位后,封务勿尘为大单于,段匹磾为左贤王,率众助国征讨,授予抚军大将军。)zhidao
形容词的情况下,他的词义与文言文列举如下:
炰鳖鲜鱼。——《诗·大雅·韩奕》
芳草鲜美。——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根色鲜泽。——宋·沈括《梦溪笔谈》
衣服常鲜于我。——《汉书·广川惠王越传》
饫肥鲜者。——明·刘基《卖柑者言》
无鲜肥滋味。——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葬鲜者自西门。——《左传·昭公五年》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大雅·荡》
原小则鲜。——《史记·货殖列传》
以约失之者鲜矣(由于俭约而犯过失的人很少)。——宋·司马光《训俭示康》
菊之爱,陶后鲜有闻。——宋·周敦颐《爱莲说》
鲜不疫矣。——清·方苞《狱中杂记》
动词的情况下,他的词义与文言文列举如下:
既无叔伯,终鲜兄弟。——李密《陈情表》
刘珝,字叔温,寿光人。正统十三年考中进士。改为庶吉士,授官编修。天顺年间,历任右中允,东宫侍讲。
宪宗即位,作为旧的官僚,多次升任至太常卿,兼侍读学士,直经筵日讲。成化十年,进升为吏部左侍郎,担任讲官照旧。刘翊每次进讲,反复开导,语气从容不迫地,听到的人都为恐惧。学士刘定之称为讲官之一,宪宗也很重要的。第二年,诏令以本官兼翰林学士,人值文渊阁参与机要事务。皇帝每次都叫他“东刘先生”,赐印章一,文章说“嘉猷赞翊”。不久升任吏部尚书,再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文华大训》成功。加官太子太保,升任谨身殿大学士。
刘翊性格开朗直爽。自认为官僚旧臣,遇到事情不回避。员外郎林俊因为弹劾梁芳、继晓被关进监狱,酸在皇帝面前的解释。李孜省等人左道乱政,想动摇太子。刘翊秘密上疏劝谏,计划少受阻。一向轻视万安,曾经斥责万安辜负国家没有羞耻。安积忿,日夜思念中酸。当初,商辖弹劾汪直的,刘翊和万安、刘吉帮助之争,结果罢除西厂。有一天,刘翊又在朝堂责备王越,王越羞愧而退。不久西厂重新设置,酸不能有所争论。到十八年,怎么看到直失宠,揣测西厂应当停止,邀请刘翊一齐演奏。刘玥推辞不与,万安于是独自上奏。奏疏呈上,皇帝很惊讶没有刘瑚的名字。安暗中派人揭发刘翊和直有牵连。恰逢刘翊的儿子刘镒邀约***狎饮,里人赵宾戏是《刘公子曲》,有时增加添饰淫秽的话语,杂教坊院本中演奏的。皇帝非常愤怒,决定去油脂。派遣宦官覃昌召集万安、刘吉到西角门,出帝亲手写的一封信函给他们看。安等人假装惊讶救援。第二天,刘翊上疏请求退休。他飞奔,我每月、每年隶、白银、纸币很好。其实排挤刘瑚使他离开的,万安、刘吉两人计划了。
当时内阁三人,万安贪婪狡猾,吉阴刻。刘硼稍微好,反而喜欢谭论,人的眼睛为狂躁。刘翊已经仓促撤退,而彭华、尹直相继进入内阁,万安、刘吉的党就更加稳定。刘翊当初遭逢母亲去世,守墓三年。等他回到,侍奉父亲尽孝。父亲去世,恢复房屋在墓。弘治三年死亡,谧号为文和。嘉靖初年,因为谏官的请求,赐祠庙匾额为“昭贤”,仍然派遣官员祭祀的。
福恭王朱常洵,神宗第三子。开始,王皇后无子,王妃生下长子,即为光宗。朱常洵在其后出生,母亲郑贵妃最受神宗宠幸。神宗久久不立太子,朝中内外大臣怀疑郑贵妃谋立自己的儿子,便纷纷就此事上奏,尽管许多人相继被贬官放逐,但仍不断有上奏反对者。神宗为此十分苦恼。万历二十九年(1601)才立光宗为太子,而封朱常洵为福王,福王的结婚费用达三十万,营造洛阳的宫邸达二十八万,是平常规定的十倍。廷臣请求福王前往藩地,为此上奏数十上百次,均未获答复。直到四十二年,神宗才命他启程去藩地。
在此之前,海内兴盛,皇帝所派税使、矿使遍布天下,每月都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堆积如山,其他搜括盈余数以亿万计。现在这些财宝大多用来资助朱常洵了。朱常洵临行出宫门时,神宗四次将他召回,嘱咐他三年入朝一次。并下诏赐其庄田四万顷。经有关官员力争,朱常洵也上奏推辞,才减去一半庄田。中州肥土不足,便选取山东、湖广之田加以补充。朱常洵又上奏请求得到已故大学士张居正被抄没的家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四川盐井专卖和茶税。伴读、承奉诸官,借管理庄田为名,乘车出入黄河南北、齐楚之间,所到之处都被他们扰得不得安宁。朱常洵又请求得到淮盐一千三百引,在洛阳设店与百姓进行交易。宦官到淮、扬供盐,他们从中侵吞,动辄就要求数倍之盐。而中州以前食用的是河东盐,因改食淮盐的缘故,凡非福王店铺所出食盐则禁止出售,河东盐引被阻止通行,边饷因此不足。廷臣请求改由河东供盐给福王,并且不再与百姓进行交易。这个建议未被采纳。神宗久居深宫,对群臣的奏章一律不予察看。唯独福王的使者记名于门籍,由中左门进出宫中,一日之内数次提出要求,早晨上奏,晚上即可得到满意的答复。四方奸人纷纷改名换姓,逃亡在外,探听风声,趋利若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万历年终之时。
到崇祯帝时,朱常洵地近位尊,朝廷尊之以礼。朱常洵终日闭阁酌饮醇酒,所爱唯有妇女、歌舞。秦中流贼四起,河南也遭大旱、蝗灾,人们互相残食,民间一片杂乱,都说先帝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洛阳富于皇宫。经过洛阳的援兵喧嚷道“:王府有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子死于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正住在家中,听说之后很害怕,便将其中利害关系告知朱常洵,而朱常洵并未放在心上。十三年冬(1640),李自成接连攻陷永宁、宜阳。第二年正月,参政王胤昌率军警戒防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也各自引兵而至。朱常洵把三将召入宫中,摆酒设宴,倍加礼待。数日之后,贼军大至,攻城。朱常洵拿出千金招募勇士,缒城而出,手持长矛冲入贼营,贼军才稍微退却。夜半时分,王绍禹的亲军从城上招呼贼军,互相谈笑,挥刀杀死防守城墙的士兵,焚烧城楼,打开北门引贼入城。朱常洵缒城而出,藏匿于迎恩寺。第二天,贼军跟踪而至将其捉拿,朱常洵就这样遇害。两名承奉伏尸而哭,贼军揪住他们,让他们离开。承奉挣扎着喊道:“福王已死,我们也不愿再活,只求一付棺木收容福王尸骨,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无怨言。”贼军见他们这么有义气,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一付桐棺,载于断车,两人就在旁边自缢而死。王妃邹氏及世子朱由崧逃往怀庆。贼军火烧王宫,大火持续三日,仍然不绝。此事传至朝廷,崇祯帝震动悲悼,辍朝三日,命河南官府为福王改殡。
早年跟同乡邹元标接受教育,跟自己的父亲李廷谏一同考中万历三十一年(1603)乡试举人。他们父子两个互相激励,身穿布衣,徒步到京师参加会试。
第二年,邦华考中了进士。他初任泾县知县,政绩优异,受到吏部的考察、推荐,本来朝廷打算升用他为御史,正碰上当时党派争论刚刚发生,朝臣很多人攻击顾宪成,邦华跟他们意见相反,就被看成是东林党人。
因此,过了两年他才接到这一任命。上任以后,邦华上书讲了十条关于效法祖宗用人办法的意见:一、内阁不应当专门用翰林院出来的词臣;二、词臣不应当专门担任翰林院的职务;三、词臣不应当到宫廷里边的书房中担任教习;四、六科都给事中不应当有能出入朝廷不能出入宫廷的限制;五、御史的升迁不应当一概取决于任职期满后的考核;六、在吏部请了假的官员不应当累计资历做到正郎;七、守关、守仓等差使不应当专门使用举贡、任子;八、调换、选拔、推举出来的地方官不应当一下子就当上京官;九、进士改充教职不应当都专门使用举贡、任子;十、边方州县的长官不应当都任命举人来充任。
这篇奏疏交上后,神宗未予答复。四十一年(1613),福王到自己封地去的时间已经决定,神宗忽然传下圣旨要求给福王的庄田务必达到四万顷。
廷臣吃惊地互相看着,估计田数一定不足,那么福王到封地去的时间又要改变了,但是没有人敢抗言争论。邦华首先上书议论,廷臣于是相继起来争论,福王到藩地去的时间才决定下来不再改变。
邦华又曾经去巡视银库,上书列了十条祛除弊端的办法,宦官认为对自己不利,就给挡了回来,没被采纳。后来邦华去巡按浙江,织造中官刘成死后,朝廷命令把他的事务交回给官府来办,又另外派遣了一名中官吕贵来收取刘成的遗产。
吕贵教唆一名坏人纪光假称机户到京城来请求留下吕贵,让他接替刘成督办织造。邦华上书极力讲述他们两个人互相勾结弄虚作假的罪恶。
纪光的上书不通过通政司,也没发下给内阁,最后用宫廷里直接传下圣旨的办法实现了他们的目的。邦华三次上书争论,神宗都没有答复。
当时神宗贪财,中官有所进献,都被称为孝顺。邦华的奏疏批评到了这一点,并且弹劾神宗左右偏袒吕贵的大宦官。
因此邦华任职期满后,长期没人去接他的旧任。四十四年,邦华称病回乡。
当时一群小人都在竭力排挤东林,把邹元标指为党魁。邦华与元标是同乡,相互之间是师友关系,他的脾气又喜欢辨别是非。
有人劝他做人要圆滑一些,邦华说:“我宁为偏枯的学问,不做反复的小人。”那些人听说后更加恨他了。
第二年,根据年限规定把邦华调出,让他去做山东参议。他的父亲廷谏当时任南京刑部郎中,也被罢官回家了。
邦华于是就推辞生病,没有去赴任。天启元年(1621),邦华起复原任,前往整顿易州兵备。
第二年,他升为光禄少卿后,回家看望父亲去了。四月,朝廷提升他为右佥都御史,让他去接替毕自严巡抚天津。
当时天津的军府刚刚开设,各项事务都是草草上马,邦华到任后极力加以整顿,使津门军成了各镇的表率。邦华升任兵部右侍郎后,又返回家乡探望父亲。
四年春天邦华抵达京师,阉党大吵大闹,说枢辅孙承宗在万寿节来朝见皇上时将要“清除皇上身边的坏人”,事实上是邦华引他来的。熹宗皇帝立刻勒令承宗返回驻地,邦华自己请病假回去了。

第二年秋天,阉党弹劾并削除了邦华的官籍。崇祯元年(1628)四月,邦华起任为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
不久改任兵部右侍郎,协理军政。邦华回到朝廷,受到庄烈帝召见,过后主持了武会试,事后进到军营中。
按照惯例,皇上冬至祭天,部队列队护驾,用兵八万五千人,当时增加到了十多万人。当时庄烈帝正要祭天,总督随行部队的勋臣缺乏人选,就让邦华兼管这件事。
邦华所布置的云辇、龙旌、宝纛、金鼓、旗帜、甲胄、剑戟都焕然一新,庄烈帝很高兴。第二年春天庄烈帝视学,邦华又布置得很好。
庄烈帝命令给他加官为兵部尚书。当时兵政十分乱,邦华首先提出要改变操练 *** 、慎重选择将吏、改造战车、精制火药、集中武器、责成防官、节约金钱、酌情兑马、演习大炮等九件事。
京营一向有占役、虚冒的弊端。占役就是士兵为诸将服劳役,一个小营中这样的士兵能达到四五百人,并且还有卖闲、包操等弊端。
虚冒就是部队没有这么个人,诸将及勋戚、宦官、豪强以自己家的仆人冒充军队中的壮丁,每个月支取一份厚饷。邦华加以清查,收回了占役士兵一万人,清出虚冒一千人。
三大营兵力十多万人,有一半是老弱之人。按照惯例,京营部队名额短缺时允许报加,这些老弱之人大都是通过贿赂进来的。
邦华对各营士兵都亲自加以考试,不是年轻力强的一概不录用,从此京营中很少有随便充数的士兵了。三营中选一万名先锋,七千名壮丁,他们的军饷比别的士兵多一倍,但是也一样是些虚弱不堪的士兵。
邦华下令,每个把总手下五百士兵,每个月自行从中挑选五个人,年龄必须在二十五岁以下,力气必须在二百五十斤以上,本领必须是兼能弓箭火炮,每个月选送一回,添补先锋、壮丁的缺额。从此部队中人人都想要努力了。
甫里先生,人们看见他在甫里耕种,所以这样叫他.先生的个性放纵不拘,喜欢读古代圣人的书,其中最喜欢《春秋》,挑出其中的小毛病.看见文中子王仲淹所写的一本书,其中说“《春秋三传》写出之后,《春秋》就失去其意义了”,他很赞同这种观点.韩晋公曾经写了《春秋通例》,把它刻在石头上,竟然把这种研究学问作为自己一生的任务,并且书中的内容颠倒混乱,没有一处通顺.经过大概百来年,没有谁敢指出其缺点错误.甫里先生担心误导青年人,就写书挑出其中毛病进行辨正.先生平时以读写文章自娱自乐,从来没有稍微放弃过.每写成一本,有的被喜欢的人拿去,后来在别人家发现,也不再说是自己的作品了.少年时钻研诗歌,他写的诗歌,最初时追求奇险怪异,如同破阵对敌一样,到后来达到了平和淡雅的地步.每得到一本书,滚瓜烂熟之后才放回搁置典籍之处.他只要发现哪本书中有错谬之处,立即提笔修改,不以两三次为限度.红、黄两种笔,没有一天从手中离开.借别人的书,那些装订有损坏的,他重新装订好,有文字谬误的,他就勘正.他很高兴听见别人做学问,评讲谈论不知道疲倦.先生虽然家贫,却从来不谈获取利益.先生的居处,有几亩池塘,有三十间房屋,有四百亩田地,不只有十头牛,有五六个农夫.但是他的田地地处低洼之地,只要下一昼夜的暴雨,就与江水连通,分别不出是自己的田还是别人的田了.先生因此受到饥饿的困苦,粮仓里没有一点积蓄,只好亲自带着农具,带领农夫修堤筑坝.从此每年虽然洪水猖狂,也不能跳过他的提防、淹没他的庄稼了.有人讥讽先生,先生说:“为了治水,尧身体瘦弱,舜脸色发黑,大禹手脚打起了硬茧,不都是圣人吗?我只是个老百姓而已,如果不勤劳辛苦,用什么给妻子儿女维持生计呢?况且这同那些名器上的蚤虱、粮仓里的雀鼠有什么区别呢?”先生生性不喜欢同鄙俗之人结交,这种人即使到了门前也见不到他.先生不准备车马,不参加庆贺吊丧之事.家族内外的亲戚朋友,过年过节婚丧嫁娶,他从来没有按时参与来往.有时不冷不热,身体很好又无事之时,先生就乘坐小船,准备帐篷和桌席,只带着一卷书、一套茶具、一副笔墨、一套钓具和一个摇船童子而已.他所到之处有一小点不合意,就径直回来不停留,即使是水鸟腾飞、山鹿惊跑也比不上那么快.人们叫他为江湖散人,先生就写了一篇《江湖散人传》来歌咏.从此,无论是赞赏还是诋毁都不再受影响,对他进行批评或者表扬的话他也不再放在心上.先生个性耿介急躁,遇到事情就立刻发作,总是不能隐忍.不久又后悔,多次改正都不能改掉这个习惯.先生不传播自己的姓名,社会上也没有人知道他,他难道不是像涪翁那样的钓鱼人、打渔的船夫之类的人吗?。
三、东海王司马越怎么死的
“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琊王与琅琊王氏的地域结合,又有其历史原因。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即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八王之乱后期,惠帝子孙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为其时司马皇族中血统最近的亲属。成都王颖抢得了皇位继承权,称皇太弟,居邺城遥制雒阳朝政。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后参与乱事的藩王。按血统关系说,东海王越是司马懿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于武帝、惠帝皇统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颖居于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样。按食邑数量说,成都王本食四郡,东海王只食六县,大小轻重迥不相同。永兴元年(304年)七月荡阴战后,惠帝被劫入邺,成都王颖更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党于东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邺,成都王颖和惠帝以及皇室其它近属逃奔雒阳,被河间王颙部将裹胁入关。这时候,惠帝兄弟辈25人中,只剩下成都王颖(原来的皇太弟,入关后被废)、豫章王炽(入关后新立的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和吴王晏(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之父)。惠帝和宗室近属悉数入关,广大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这是东海王越填补空缺、扩充势力的大好时机。东海王越的势力就是趁这个机会扩充起来的。荡阴败后,司马越回东海国,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进行了大量的活动。从此,徐州地区成为他的广阔后方。他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镇以为形援。然后他移檄征、镇、州、郡,自为盟主,并于光熙元年(306年)把惠帝从长安夺回洛阳。接着,惠帝暴死,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被害,继立的晋怀帝完全在司马越的掌握之中。司马越在皇族中已没有强劲的对手,八王之乱至此告终。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军队动辄威胁洛阳,使司马越不遑宁处。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号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关东是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统治的命运。但是关东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样,在十几年的大乱中受到摧残。有些人鉴于政局朝秦暮楚,尽量设法避祸自保。名士庾敳见王室多难,害怕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宣扬荣辱同贯,存亡均齐思想。还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吴士张翰、顾荣辞官南归,颍川庾衮率领宗族,聚保于禹山、林虑山。这种种情况,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动向。司马越必须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够影响的人物列于朝班之首,才能号召尽可能多的士族名士来支持他的统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马越看中,他们密切合作,共同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王衍郡望虽非东海,但是是东海的近邻。王衍家族的社会地位,高于东海国的任何一个家族。王衍是其时的名士首领,以长于清谈为世所宗。据说此人终日挥麈谈玄,义理随时变异,号曰“口中雌黄”,朝野翕服。《世说新语》一书,记载了清谈家王衍的许多佚事。不过王衍的玄学造诣,声大于实,史籍中除了记他祖述何晏、王弼“贵无”思想和反对裴頠的“崇有”之说等寥寥数语以外,不言他对玄学究竟有什么贡献。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竟找不到王衍谈玄内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死前曾说:“呜乎!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从此,王衍就以清谈误国受到唾骂,至于千百年之久。王衍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口头上虽说“不以经国为务”,自称“少不预事”,但青年时代就“好论纵横之术”。以后除了一个短时间以外,王衍始终居于朝廷高位。王衍之女,一为愍怀太子妃,一适贾充之孙贾谧。可见他在西晋末年宫廷倾轧这一大事中既结后党,又结太子,两边观望,期于不败。王衍另一女为裴遐妻,而裴遐是东海王司马越妃裴氏从兄。王衍通过裴遐,又同东海王越增加了一重关系。以上种种,都是王衍所结的政治婚姻,反映王衍在政界活动的需要。他被石勒俘获,临死犹为石勒“陈祸败之由”,并且“劝勒称尊号”。他恋权而又虚伪,服膺名教与自然“将无同”的信条。他和司马越作为西晋末代权臣,除了操纵皇帝,翦除异己,羁縻方镇,应付叛乱以外,没有推行过任何有积极意义的措施。司马越与王衍,是一种各有图谋的政治结合。司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当时北方名士团聚在王衍周围的,数量很多,其中的王敦、谢鲲、庾敳、阮修,号为王衍“四友”。由于王衍的引荐,诸王、诸阮以及谢鲲、庾敳、胡母辅之、郭象、卫玠等名士都被司马越所延揽,南士也有辟司马越府者,所以史称越府“多名士,一时俊异。”这些人祖尚玄虚,多半没有政治能力,在司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梦死,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他们之中多数人陆续过江,庇托于江左政权;有些名士则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杀。东海王越妃出河东裴氏。西晋时裴氏与王氏齐名,时人以两家人物逐个相比,以八裴方于八王。裴妃兄裴盾、裴邵,都是司马越的重要助手,也是司马越联系士族名士的又一桥梁。不过裴盾、裴邵没有来得及过江。裴邵随司马越出项,死于军;裴盾后降匈奴,被杀。裴氏与司马越个人关系虽密,但其家族不出于河南,与司马越府椽属多出于河南士族者,毕竟有所不同。这种河北河南的畛域之见,当渊源于昔日司马颖居邺、司马越居雒阳(今洛阳)而相互对立的历史。所以裴氏家族重要人物与其他河北士族一样,罕有过江者,因而裴氏家族没有在东晋政权中取得相应的地位,以继续发挥象王氏家族那样的政治作用。由上可知,惠帝末年和怀帝时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质上就是司马越与王衍“共天下”。可以说,这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种组合,一个形态。在司马越、王衍操纵之下,另一个王与马相结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这就是晋琅琊王司马睿与琅琊王导在徐州开启的局面。王氏家园所在的琅琊国,是司马睿的封国。司马睿的琅琊国与司马越的东海国相邻,都在徐州。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曾出为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晋书》卷三八本传称其“镇御有方,得将士死力。”后来,当司马越收兵下邳,准备西迎惠帝时,起用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后迁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为他看管后方。司马睿受命后,请王衍从弟、参东海王越军事的王导为司马,委以重任。由司马越、王衍在雒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王导在司马睿军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司马越物色司马睿,还有历史渊源。司马越与司马颖对峙之时,司马睿与其从父东安王司马繇先居雒阳,后居邺城。那时司马越已通过辟于越府的王导对司马睿施加影响。荡阴战后,司马繇被司马颖杀害,这更坚定了司马睿在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之争中投向东海王越一边的决心。司马睿在王导劝诱下南逃雒阳,转回琅琊国,在那里接受了司马越的号令。从种种迹象看来,司马睿、王导同莅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组合,而是司马越、王衍精心的策划与安排。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下邳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都是日后建康“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不过,情况还是有区别的。雒阳司马越、王衍的组合,掌握实权的是司马越;而徐州下邳司马睿、王导的组合,王导却起着主导作用。那时,司马睿还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可以把司马睿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王导传》叙述这一段关系时说:“〔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琊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雒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透过这一段夹杂着攀附之辞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睿在北方所经历的大事,几乎全出王导的主动筹谋。王导在邺城、雒阳、下邳,早已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很像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了秦国的子楚一样。子楚曾约定分秦国与吕不韦共之,而司马睿后来实际上与王导共享东晋天下。永嘉政局,纷乱异常。刘渊等交侵于外,怀帝、司马越构嫌于内,州郡征镇叛服不常,流民暴动此伏彼起。司马越、王衍力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控制,抢据要冲,以维持残破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王导南渡建邺。这是司马睿、王导同镇下邳两年以后的事。其时,王衍为门户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案指中原)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雒阳),足以为三窟矣。’”孙盛《晋阳秋》记此事,谓王衍辞诸弟时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依孙盛所记,王衍经营“三窟”,并不是消极地效狡兔之求免于死,而是欲乘王室卑微之时图谋霸业。以后的事实表明,王衍追求的霸业没有实现于齐楚,而实现于扬州的江南;不是假手于王澄等人,而是假手于王导。这是王衍始料所未及的,因为他设想的“三窟”均在长江以北,并未包括扬州江南部分。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所派生出来的。扬州江南窟成,齐楚已乱,王马天下,只有于此经营。但是此时雒阳尚有怀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势暂时还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导在建邺“潜怀翼戴之计”,待机脱离洛阳以称霸江左的事实,谓其时江左“阴气盛也”。这反映晋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时人的估计之中。司马睿渡江一举,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左立业局面。不过这不是司马越、王衍的初衷。在司马越、王衍的全盘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司马睿、王导受命过江,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这一点与江左原来的政治形势有关,将在本文下节详论。从经济上说,很可能有替坚守中原的司马越、王衍搜括江南财富,特别是潜运江南粮食的目的。原来,陈敏在洛,为尚书仓部令史,建议于执政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潜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因此陈敏得以出为合肥、广陵度支。他后来击败石冰,割据米谷丰裕的扬州江南诸郡,也得力于所统运兵。《水经·淮水注》谓陈敏于中渎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以改变湖道纡远状况,缩短了江淮间的航程。此事内容尚有疑点,不可全信,亦非全诬。《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顾野王《舆地志》,谓陈敏在丹阳境开练湖,而练湖之开与维持丹阳、京口间运河航道有密切关系。《舆地纪胜》卷七引《舆地志》,谓京口城南有丁卯港,港有埭,为京口运河航道重要设施,据说“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司马裒镇广陵,开丁卯埭,为建武元年(317年)事,在陈敏于扬州江南开练湖以济运河之后十年。这些维修江南运河的史实,都与陈敏离都的初衷切合。又,司马睿、王导在徐州时本有漕运任务。徐州治所下邳,当泗水通途。《水经·泗水注》:宿预,“晋元帝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司马睿与王导南来,沿中渎水下广陵,过江而达建邺,也是踵陈敏之迹。根据这许多迹象,我推测,司马睿、王导奉命南来,本有与陈敏相同的潜运江南粮谷以济中州的经济目的。细察王衍“三窟”之说和其后事态发展,可以认为司马睿、王导受司马越、王衍之命南来,并不是为越、衍南逃预作准备。司马越和王衍始终不见有南逃的打算。我们知道,司马越是在逗留东海、收兵下邳以后才得以成为独立力量的。他的军队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东海国人为多。雒阳宫省宿卫,也都被司马越换成东海国将军何伦、王景的东海国兵。永嘉四年(310年)冬司马越声称为讨伐石勒而离雒,还以何伦和坚决支持司马越的“乞活”帅李恽等军,奉东海王妃裴氏和世子毗守卫雒阳,监视宫省。这些情况,说明司马越、王衍势力的地方色彩很浓。他们只求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不曾考虑偏安江左。其时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寿春,也被拒绝,周菠以此为司马越、司马睿的军队夹攻致死,这就是史臣所谓“祖宣(馥字)献策迁都,乖忤于东海”一事。司马越的战略意图,是依托徐州,守住洛阳,自为游军与石勒(以后还有苟晞)周旋。王衍是支持司马越这一战略意图的。当雒阳由于刘渊、石勒的攻击而人心浮动,迁都避难呼声甚紧时,“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后来,司马越、王衍拥军东行,越于道中病死而托后事于衍,衍必欲扶越柩归葬东海,以至于在东行道中为石勒部众追及,王公士庶十余万人俱死。何伦、李恽拥裴妃及世子毗逃离雒阳,世子和36王都落入石勒之手,何伦东走归下邳,李恽北走广宗,时在永嘉五年(311年)。司马越、王衍拥众东行,从战略战术上看不出有其它用意,只是反映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将士“狐死首丘”的愿望而已。《晋书》卷三五《裴楷传》载东海王越妃兄徐州刺史裴盾大发良人为兵,司马越死,裴盾“骑督满衡便引所发良人东还”,也是东方将士只图奔返家乡之证。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而无南渡意图,客观上便利了司马睿、王导在江左独立经营。东方青、兖、豫、徐诸州士族名士则多有在胡骑侵逼之下南走建康者,昔日司马越府俊异陆续归于司马睿府,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有助于司马睿、王导势力的壮大,而且也显示出麇集江左的这一集团是雒阳朝廷事实上的继承者。尔后江左的门阀士族,大体上都是出于昔日司马越府的僚属。与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成为对照的,是阎鼎的西行。阎鼎,天水人,也出于东海王越府参军。他鸠集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里。雒阳沦陷后,他翼戴秦王(后来的晋愍帝)西奔长安。裹胁而行的以荀藩、荀组为首的行台诸人多关东人,不愿西去,或者逃散,或者被杀。由此可见,其时除有前述河南、河北的畛域之分以外,还有关东、关西的畛域之分,这在士族人物中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影响着政局的发展。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吴人孙惠在上司马越书中说:“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王衍一伙惨死在石勒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尸骸。他们在北方彻底失败了。残存的长安朝廷落入西州人之手,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只有他们派出的司马睿和王导,在建邺植下了根基。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琊王导。这样,在北方具有雏形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为一个新朝政权的基本结构。
关于王越死亡时间到此分享完毕,希望能帮助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