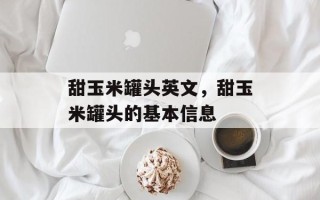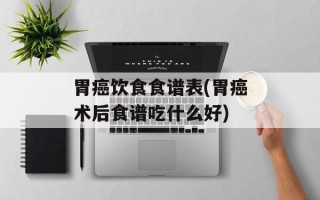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分享上海大中里的一些知识,其中也会对上海徐家汇小区进行解释,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就马上开始吧!
本文目录
一、上海静安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上海静安有许多好玩的地方,以下是一些推荐的地方:
上海自然博物馆。静安的遛娃胜地,馆内植物、鱼类、鸟类等标本约有29万余件,还有身长22米的合川马门溪龙等展品,是寓教于乐的好地方。地址:北京西路510号,开放时间为09:00-17:00(周二至周日)。
石二红色文化区域(含静安雕塑公园)、彭湃故居、 *** 劳动组合书记处旧址。可以领略大隐于市之风,该地区有刘长胜故居、1920年 *** 旧居等红色文化点位,还有上海最古老的佛寺——静安寺。
静安寺地区。作为静安标志性地标区域之一,东起常德路,西至华山路,南起延安西路,北至愚园路。该地区除了有刘长胜故居、1920年 *** 旧居等红色文化点位外,还有上海最古老的佛寺——静安寺。
静安环大中里区域和上海展览中心。南京西路重要景观节点,太古汇、越洋、嘉里、梅泰恒等大楼实施景观灯光提升,塑造“光连南西、贵雅相融”的整体夜景效果。
延中绿地静安段。位于静安区延安中路和老成都路交汇处,面积为3.48公顷。
上海市,简称沪,别称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上海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世界一线城市。上海市总面积6340.5平方千米,辖16个区。 2022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475.89万人。
上海市位于中国华东地区,地处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一部分,介于东经120°52′—122°12′,北纬30°40′—31°53′之间;上海市平均海拔高度2.19米,大金山岛为上海更高点,海拔高度103.7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河网主要有流经市区的主干道黄浦江及其支流苏州河、川杨河、淀浦河等。
二、大中里的历史追溯
今石门一路214弄。位于静安区东南部,属南京西路街道大中居委会。占地19.69亩。上世纪初,此地曾是一片农田(间有杂草丛生的墓地)。1925年颜料商奚鹤年以其妻刘莲仙的陪嫁地产,在此投资兴建房屋。因为当时在华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多以“大英”、“大日本”自称其国,故业主即以“大中”命名此弄,表示“大中华”之意。旧式里弄。总弄宽敞,各支弄排列整齐,有砖木结构二层房屋111幢,建筑面积14699平方米。弄内有区物资回收利用公司。原有居民535户,约2400人。附近有23、41、49路公交车辆驶经。
大中里的西侧为石门一路(同孚路Yates Road也称宴芝路),是上海1920和1930年代高尚时装街。北侧为著名的美食街和时尚休闲街吴江路,离南京西路一步之遥,这里交通方便,地理位置独特,不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上海国际大都市高档和时尚的尊贵席地
三、静安区大中里的建筑历史
静安区大中里地块启动保护历史建筑移位工程
民立中学老校舍位于石门一路威海路附近的“大中里”
3月10日上午,静安区大中里地块启动保护历史建筑移位工程,有近90年历史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民立中学老校舍,将被平移到约50米外的威海路边。
民立中学老校舍是一幢中西合璧的花园洋房,建于1920到1930年间。
为上海滩著名颜料巨贾邱信山、邱渭卿兄弟所建,原为两幢,其中一幢于上世纪90年代拆除,被迁移的这幢曾是民立中学办公楼,于1999年被评定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它檐部山墙为巴洛克式,二层中部设有欧式外廊,北立面则有中国江南建筑特色。
据介绍,10日启动的大中里项目位于石门一路威海路,毗邻南京西路,占地约6.3万平方米,将建设成包括商业购物中心、办公楼及酒店的大型综合性项目。
民立中学老校舍,位于轨道交通13号线一出口处。
经市、区有关专家反复论证,决定将老校舍平移。
因为有上海音乐厅平移的成功经验在先,这一建筑保护技术已比较完善,一般是先将原有建筑加固保护,随后把地基整体移动到新架设的轨道上,再用千斤顶缓缓推移。
这一平移工程预计在半年内完工。
此外,该地块内还有一棵百年玉兰树,也将在原址保护。
四、大中里的工程概况
1、大中里综合发展项目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区域附近,项目由静安区40号、46号街坊两个地块组成,整个项目地块东到青海路,南到威海路,西到石门一路,北到南京西路。46号街坊在整个地块的北侧,吴江路在40号和46号街坊之间穿过。本项目是集商业、办公、酒店等于一体的综合发展项目,包
2、括三座酒店/酒店式住宅、二座办公楼和一座购物中心,本项目40号地块分布有五座塔楼,南北广场及商业裙房,各地上建筑之间有若干天桥相连,地块内还有移位的民立中学优秀历史建筑。项目整体地下4层,地下4层。46号地块主要建筑为一座商业建筑剧院(无地下室)。
五、上海太古汇一座8楼地铁从哪个口出
太古汇是太古地产继广州太古汇、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北京颐堤港、成都远洋太古里(专题阅读)后的第五个面世项目。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兴业太古汇,是由香港兴业国际和太古地产共同开发的大型综合体项目。项目占地面积6.3万平方米,总楼面面积约3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32.5万平方米,包括一个购物商场、两座办公楼、三家酒店和服务式公寓,其中购物中心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
香港兴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太古地产有限公司联合宣布,双方于上海合作发展的大型综合项目正式命名为“兴业太古汇”,项目前称为“大中里项目”。
香港兴业国际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查懋成指出,香港兴业国际于2002年购入大中里地段,作为此项目的创始合伙人,我们于2006年邀请太古地产成为合作伙伴。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我们很高兴公布项目正式命名为兴业太古汇。
而太古地产行政总裁白德利表示,我们很高兴命名太古地产在上海的首个项目为兴业太古汇,上海将再添一全新休闲好去处。
六、大中里的介绍
大中里始建于1925年的“大中里”曾经是上海市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更大的石库门里弄之一。目前已被整体拆除并成为一处地产开发项目。项目位于上海市中心静安区南京西路的核心区域,北接南京西路,西临石门一路(面对四季酒店),南邻威海路,东靠青海路(面对上海广电大厦),总占地面积6.3万平方米。轨交2号线、13号线及12号线将在项目周围的路段实现地下连通,形成换乘枢纽。被香港兴业国际称为上海“更优越”地段的静安区大中里项目将超越新天地成为上海顶级娱乐消费新地标。这也成为老牌地产巨头太古地产在上海的之一个房地产项目。原太古主席简基富表示,项目投资总额将不少于100亿元。
七、大中里的往昔印象
1、清晨5点,天色微亮,酣睡一夜的人们尚在享受最后的安宁,寂静的弄堂里已然响起了一阵“唰唰”声。
2、是“大中里”的清洁工阿跷在打扫垃圾箱,他的出现,宣告了“大中里”开始新的一天。阿跷本名袁德海,但除了唯一的大哥坚持称他“德海”,“大中里”人人叫他“阿跷”。出于尊老的传统观念,称呼一个右脚残疾的70岁老人“阿跷”,非常不礼貌,但阿跷从不介意这个称呼,因为他知道,“大中里”人人给他几分面子。这是上海旧式里弄的一个特点,称呼不能代表什么,对某个人的尊敬是靠时间积淀,并通过行动来体现的。
3、“我这活儿别人干不了。”阿跷话里透着了然于心的自豪。每天清晨,“大中里”的垃圾箱一片狼藉,石门一路沿街的小饭店趁着夜色将垃圾随意扔在那儿。阿跷要赶在人们起床前将垃圾箱打扫干净,用水冲净路面,随后锁上垃圾箱的门,只留下两个门洞用于居民丢垃圾。与垃圾箱相邻的厕所,是“大中里”唯一的卫生设备。老式的里弄住宅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几家合用的水厕,只有一个公厕,供所有住户倒马桶和痰盂。
4、阿跷锁上垃圾箱大门的同时,还得打开厕所里专供倒马桶的小隔间。这个隔间只在每天早晨6点至10点对外开放,“不能整天开着,人太多了,粪便倒多了要铺出来。”做完这些,阿跷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开始。他拿出晚上锁在隔间里的椅子,放在垃圾箱斜对面的石库门前,安静地坐着。他的工作是盯着垃圾箱和厕所,防止人们为了图方便将垃圾扔在外头,或是某些男人图省事儿、在小便池里大便。阿跷要这样独自坐到晚上6点,风雨无阻。冬天里,他就裹着民政局领导视察时赠送的棉大衣;夏天日头毒,居委会给他一把伞,他就这么一整天地撑着,遮挡阳光。
5、现在“大中里”的年轻人,弄不清阿跷坐在那里做啥。就如出生和成长在“大中里”、后又出国留学的舒浩仑,他始终认为孑然一身的阿跷喜欢坐在那里看进进出出的人们,同时义务充当“大中里”的保安。2002年,留学归国的舒浩仑得知“大中里”要拆迁的消息,扛起摄像机拍下了一部关于“大中里”、关于石库门文化的人文纪录片,取名《乡愁》,阿跷是其中一个人物。
6、“一个月就两百块,还要受气挨打,外地人干不了。”阿跷说,因为扫得干净,他曾被调去上海电视台边上的青海路,本地人不愿意接替阿跷的活,居委会就找了个外地人。但没多久对方就不干了,因为“大中里”某些居民在乱倒垃圾时,气焰还很嚣张,看到陌生人值勤,不但不买账,有时还会起冲突。“我坐在这里,‘大中里’的人都给我几分面子,住在这里的外地人看我年纪大,也会听我的。”于是阿跷又被调回来,继续充当垃圾箱和公共厕所的守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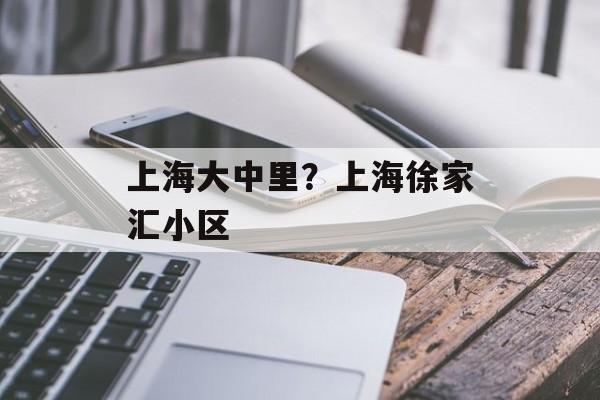
7、6点之后,安静的“大中里”顿像苏醒了一般,热闹起来。这片石库门布局非常整齐,从空中俯视,分弄与主弄的排列像是一个横过来的“丰”字。解放前就搬来这里的老人说,这是英国人提高效率的方式,把弄堂造得笔直,治安人员一眼就能望到底。
8、说“大中里”是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并不为过。1925年,“大中里”所在的静安区是英租界,作为一个英国房地产商的开发项目,这片石库门里弄也因此拥有了西式风格的雕花门楣、联排别墅式的布局。英国开发商深谙中国人的居住习惯,于是每一栋石库门都是传统江南民居的翻版:天井、前后客堂、前后厢房、亭子间和晒台。“从建筑角度讲,石库门堪称精华。”长期致力于古城保护的同济大学城市与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说,石库门既能体现西式住宅的规划理念,又保有中式民居的建筑风格,“从当时的居住条件来看,是非常舒服的。”
9、恐怕当时建造“大中里”的开发商,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条在当时为了便于管理而造得笔直的主弄,早已演变成一条充满生活气息的社区马路。主弄自北向南,依次排列着菜摊、鸡蛋摊、肉摊、水产摊,还有卖早点的。在他们面前来回穿梭的,是穿着睡衣、满脸倦容地端着痰盂走向公厕的女人,还有那些赶在上班前挑菜买肉的男人。
10、“永平爸,来碗小馄饨。”骑车的中年男子跳下车,冲着包馄饨的老伯喊。永平家的早点摊正好位于主弄的中点,摆了十多年,设备很简单:一张圆台面,六七把裹着破麻袋的靠背椅。74岁的永平爸负责包馄饨和收钱,退休前在国营饭店做厨师的永平妈负责煮食。早点式样很简单,小馄饨和汤面,夏天再增加一款冷面。舒浩仑拍《乡愁》时光顾过永平家的早点摊,但1972年出生的他更怀念小时候的那家国营早点摊。每天早晨,人们拿着茶缸排队买豆浆,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熟练做着上海人早点食谱中的“四大金刚”:大饼、油条、糍饭和豆浆。
11、那时的油条半两一根,为了方便人们买早点,上海特制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半两”粮票,以至于当时来沪的外地人,把这当成了上海人小气的一个例子。等候小馄饨的中年男子招呼着身边过往行人,“阿婆,买菜啊。”“嗨,上班去啊,不吃早饭啊!”男子津津有味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寻找熟人,毫不在意小馄饨何时端上桌。直到身边食客越聚越多,男子的注意力才开始回到圆桌。“你们知道当时四季酒店后面那些房子,拆迁时每个人拿多少钱吗?”“听说是三十多万,我们这里就隔了一条街,凭什么少了十多万。”吃着面条的食客含混不清地回答。
12、自打动迁组进了“大中里”,拆迁、赔偿就成了早餐桌上不变的话题。安贫乐道的“大中里”像是突然面对一场灾难,对未来的不可知引发的惶恐从每日的早饭开始。这群本无足够经济能量购置新房改善居住条件的普通人,在面对搬迁时不得不考虑如何为自己寻一处安身之所。围成圈吃早点的人热闹地议论着,像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直到吃完起身、互道再见时,才发现根本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13、“永平爸,收钱。”食客将两元钱递给老伯,老伯伸手接过,塞进兜里,又用同一只手包起了馄饨。不过,在“大中里”没人会质问永平爸不讲卫生,哪怕是那些略有洁癖、端着自家饭碗来装小馄饨的人。
14、舒浩仑的儿时记忆与陆芸的儿时记忆完美地进行了时空对接。陆芸是陆家阿公的外孙女,得知“大中里”要拆的那一刻,外公愣了半晌,外婆眼里泛着泪光,从小在“大中里”长大的陆芸无意中发现了《乡愁》,于是决定买张碟给家人一个惊喜。
15、陆芸出生在1981年,在她的记忆里,上海同样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陆家是所有亲戚心目中的殿堂。每逢五一和国庆,住在浦东的亲戚带上土产赶到陆家住下,只为了观看节日里的 *** ,孩子们则一早搬着小板凳在晒台上抢座位,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节日烟花。陆家的优越感持续到了九十年代浦东开发的一刻。浦东地价陡增,亲戚们一夜暴富,做起了房产开发商,便绝少出现在“大中里”。有个亲戚过节探望陆家阿公时,忍不住说:“这房子太破了。”“可我还是喜欢这里。”陆芸留恋“大中里”生活的厚重和质感。在日本公司工作的陆芸曾带一些五六十岁的日本朋友参观“大中里”,看到厨房里的灶头和屋里的马桶,他们兴奋不已地说:“我们也曾经那样生活过,真令人怀念。”
16、陈佳立和陆芸同年,出生在静安区另一处石库门群落——庙弄。八年前动迁后,庙弄原址上竖起了一座霸气的购物中心。陈佳立记得小时候和同伴跑去百乐门边乘凉,看着车来车往,如今新兴社区的孩子,只是在 *** 上构建一派虚拟的友谊世界。
17、舒浩仑想在“大中里”放映一次《乡愁》。他的乡愁,既来自于故乡“大中里”的消失,也是对石库门生活方式行将终结的悼念。毕竟,“大中里”呈现的是被光鲜外衣遮蔽了的最原汁原味的上海生活。石库门随风而逝,依附其上的上海历史和文化,也将凋零或消失。“如果可能,我还要请些模特在弄堂里走秀,你不觉得,那个年代的石库门弄堂,就是T型台的雏形吗?”舒浩仑的记忆中,每逢夏日傍晚,乘凉的男人们赤膊睡在躺椅上一字排开,这时若有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走过,无数包含带着欲望和艳羡的眼光齐刷刷地射过来,年轻女子的步履变得更婀娜,哪怕她已被一些女性长辈唤做“小妖精”。
18、“每个阶层都能从石库门里找到自己的文化梦想,他的痛苦悲伤和他的记忆。”上海文学批评家朱大可,曾在一次关于“工人新村与石库门谁更能代表上海”的辩论中说,石库门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早期的资产阶级能在这里找到昔日的梦想,过去大杂院里的市民也能从这里找到曾经的记忆,尽管记忆里面充满了很多痛苦的东西。石库门是混合了上海人爱与痛的产物(注:工人新村是1951年上海市 *** 从苏联引进的,解决了上海三百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当时能住进“工人新村”的都是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研究城市文化的学者把工人新村看作上海在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化,并据此认为形成了上海人的一种性格:比较制度化,比较容易被管束)。
19、前两个月,北京前楼附近的胡同连片被铲,一群民间人士自发冲向胡同里拍照,每天与推土机比速度。舒浩仑发了封邮件给他们,“虽然大家怀念的实物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过往传统的回忆和悼念。”这种眷恋和怀念,不仅仅局限于北京人和上海人,甚至已经远远超越了胡同、石库门等有形建筑物。在广州媒体工作的刘先生曾经打算将年幼的女儿送回江西老家上学,他说,这是因为“那些看似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更加完整地保留了传统”。只是,这一想法终因妻子舍不下爱女而作罢。
20、刘先生说,只要想起老家的房子和土地,心里就有了底气,不像他曾接触过的一些上海朋友,当从小居住的老房子被推土机推倒后,一段活生生的记忆被连根拔起,人也显得浮躁。老刘在欧洲看到那些保留了近两百年的破房子仍被使用着,明白这是人家城市化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后的觉醒,于是他做了一回有心人,购买新房时没有出售原来的住处,“我的女儿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等她成年了,能去老房子找回忆。”
21、三毛曾说,少年的她每当看到世界地图上撒哈拉沙漠那一片赤黄的时候,心头总会泛起一种乡愁,于是终于有一天她背起行囊,哼着“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近年来在全国兴起的读经运动、国学热和海外汉学热,抑或同样有迹可寻?余光中的一首“乡愁”,曾经感动海峡两岸30余年,那是台胞甚至是海外华人共有的思乡之情。而多年之后,余光中才慢慢意识到,他的乡愁其实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22、6月25日,《乡愁》在上海虹口区图书馆公映。那天下午,看完片子的人们走在街上,默默地将镜头对准了虹口区老街上的房子。作为嘉宾出席放映活动的陆元敏是上海著名的影像记录者,曾出版过苏州河与石库门的影集。在拍下一张堆放着杂物的石库门屋子时,他说,很多年后,那些已经生活在宽敞整洁楼房里的人们,应该会被这张照片打动,进而引发对逝去岁月的缅怀。
关于上海大中里,上海徐家汇小区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